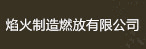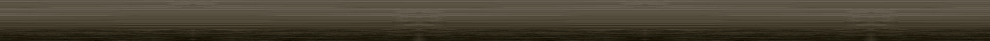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人的烟花燃放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烟花爆竹不仅是年味的象征,更是传统故事里驱赶年兽、祛病驱邪的精神寄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民俗专家陈华文说,“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在爆竹声声中过年,是持续了千年的中国式浪漫。”燃放烟花爆竹这个习俗大约在唐宋时期就开始流行了,古人在描写节日的诗词里时常出现和烟花爆竹燃放有关的句子,比如王安石《元日》中“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再比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但近年来,烟花爆竹的“禁”与“放”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每到春节前夕,随着各地烟花禁限放政策的出台,烟花爆竹“禁”与“放”的话题讨论都会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今年,随着防疫政策的逐步放宽,这个争论似乎尤为激烈。一时间,“禁”有“禁”的道理,“放”有“放”的问题,莫衷一是。
长沙浏阳作为烟花之城,烟花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谓不强,浏阳花炮更是名声在外。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数据,2021年浏阳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261.5亿元;2022年,全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301.5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花炮出口销售额超过60亿元,同比增长84.9%。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因为花炮行业的吸纳,浏阳市的人口也几乎没有外流,对当地人来说,花炮是富民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让很多乡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橘洲焰火,曾是长沙十大网红打卡圣地之一,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观赏,不仅带动了长沙的旅游业,也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张靓丽的名片。近年来,受到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已经基本取消了烟花燃放的活动,不得不说这对长沙的旅游业发展和城市形象的提升也带来了不小影响。
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教授说过,“文化传承如果没有形式上的载体,又有谁有兴趣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味呢?”。没有了爆竹声声,没有了烟雾缭绕,好像就品不出春节的喜庆,看不到节日的氛围。没有了形式和气氛的营造,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没有动力去了解春节背后的典故和习俗。想要文化不被剽窃,不被拱手让人,必须要形成全民性的文化思考与理解,而烟花爆竹的燃放也是助推这种格局形成的一种媒介。当然,除了放鞭炮,我们也要结合其他形式,比如春联,面花,年画,舞龙等等仪式感的内容共同传承中国年俗的历史文化。
烟花燃放具有明显的地域零散性、时间集中性、人员复杂性、查找隐蔽性,烟花燃放主要集中在清明、春节等法定假期,且燃放的地点分散不均,很难组织调配足够的执法力量进行劝导和查出,并且固定证据的难度非常大。据了解,2019年长沙市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政案件187起,处罚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人187人,2023年,仅湘江新区节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就排查经营门店2130余家次,收缴各类烟花爆竹100余箱,发放各类告知书2100余份,停业整顿违法经营门店1家,移送公安机关处置2人。另外烟花燃放的主体人员多样,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难以进行有效惩戒和查处。由此可见,烟花禁放的查处不仅实施起来实际困难大,而且会牵扯大量的人力物力。
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有的人认为春节放烟花就是一天的事情,一年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数据显示,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每年正月初一,全国往往出现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尤其是2017年全国66个城市PM2.5达重度污染,26个城市达严重污染,范围覆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汾渭平原、四川盆地、内蒙古中部等区域。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曾表示,烟花爆竹燃放增加了新的污染物排放,部分城市在污染峰值期间,烟花爆竹对PM2.5的贡献率最高可达80%左右。从近几年全省春节前后空气质量AQI的数据变化来看,烟花爆竹的面源式集中燃放极易形成污染过程,且累积速度和级别均超出预期。长沙市除2020年外,近五年大年初一空气质量均接近或达到重度污染等级,2023年21—22日(除夕——初一)烟花爆竹集中燃放时段对全市PM2.5贡献率达43.4%,除夕晚上个别站点PM2.5小时浓度一度高达983微克/立方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消除重污染天气,同样是民心所向的大问题!
烟花爆竹产生的噪声污染也不容忽视。数据表明,烟花爆竹产生的噪音最大值高达150分贝,接近人体承受度的两倍,堪比大型工业企业的噪音。当耳朵受到超过承受能力的噪声刺激时,即使自己感觉不出来,脆弱而敏感的耳神经也会受到伤害,造成“爆震性耳聋”。超过110分贝甚至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
烟花爆竹毕竟是火药,不管是生产、销售还是燃放过程中都可能引发火灾或者安全事故。2012年除夕至元宵节,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情192起,致伤272人,致死1人。另外,由于青少年缺乏安全意识和安全常识,爆竹伤人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让人痛心。
烟花的“禁”与“放”,背后是一道文化、人情、环保、安全等综合在一起的选择题。说到底,我们很难非黑即白地作为一道单选题来做,而是要在生态文明思想、传统文化理念、生活生产安全、经济稳定发展等多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和最优解,解决“既要又要”的问题。既不能一刀切式地全面禁止,又不能不负责任地一放了之。
禁要有禁的原则,放也该有放的灵活。一方面,应该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禁放制度,杜绝粗暴式、作秀式的禁燃令。鼓励部分城市结合环境空气、气象的研判,有限度、分区域的允许一定程度的烟花爆竹燃放,亦或是换做由政府主导、市民观看的形式有组织、有规模的不定期组织集体烟花表演。另一方面,加大烟花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从政策扶持、税收减免、技术帮扶等方面助力更环保更安全的烟花爆竹研发,也要加大对不符合质量标准、不符合技术规范的烟花生产的查处和取缔力度,建立公平良性的行业规则。再有,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积极倡导老百姓少放或不放烟花爆竹,把关注点更多的转移到体味深层年俗文化的角度上来,避免报复性、浪费性的燃放消费,让自主选择成为一种行为规范。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和规范烟花爆竹燃放:一是进一步规范燃放区域。将原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调整为规范燃放区域,从便于监督管理的角度将规范燃放区域明确到中心城区相关街道(镇),主要是三环线以内涉及的街道乡镇全域范围。二是进一步规范燃放时段。将原禁限放时间大幅度放开,除农历腊月三十(除夕)0:00至次年正月初一24:00以及重污染天气预警、轻微污染天气管控期间外,允许在规范燃放区域燃放规定的烟花品种。三是进一步规范允许燃放烟花品种。从安全和环保的角度,缩减规范区域内允许燃放烟花品种,明确为国家《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规定的个人燃放类产品中旋转类、吐珠类和玩具类C级和D级产品,喷花类D级产品。四是规范烟花销售网点。规范燃放区域内可设立经行政许可审批的烟花爆竹零售点(烟花小屋),允许销售上述规范烟花品种。烟花爆竹销售单位应当采购符合规定的生产企业的烟花爆竹,遵守安全管理规定, 新城注册?按照销售许可证规定的许可范围、时间和地点销售烟花爆竹。五是重启橘子洲烟花燃放活动。在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节假日、重大纪念日等不定期开展橘子洲烟花燃放活动。
炸响的声音和绚烂的流火似乎最能昭示春节的浪漫,唤醒年味儿的感知。烟花爆竹的“禁”与“放”不该是一道单选题,也不该是压在老百姓心头的疑难题。无论作为一种个人情怀的期盼,一种童年乐趣的回忆,还是一种传统习俗的继承,一种本土产业的保护,我们都希望探索、寻找到“禁”与“放”间的最平衡的支点,在最大限度保证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前提下让节日气氛更加浓烈,为老百姓留住年味儿!